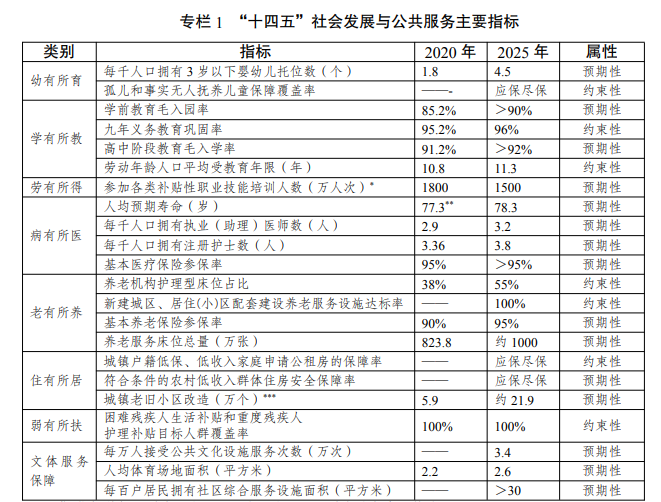这是一次期待许久的对话,从《千里江山图》面世就开始了。
一年多来,尽管专业评论和媒体报道不断,孙甘露自己一直很少“说话”。几次发去信息,他常回:“还是先听听读者的看法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第二天,孙甘露如约参加了一个谈论昆德拉的文学活动。其他嘉宾几次说到“茅奖”,他只笑笑,并未多言。活动结束后,热情的读者抱着书找他签名,向他祝贺,他耐心地签完,并一一回应:“谢谢,谢谢。”
“人大约都不喜欢被过度关注,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习惯阐释自己的作品。”这个八月,孙甘露在上海思南接受了澎湃新闻独家专访。刚刚坐定,他就带着一种略抱歉的微笑说:“我们还是不要过多地谈论作品本身吧。”
他接着打了个比方,写小说就像给读者“变戏法”,要是都跑到舞台后面去,还有什么趣呢?
“小说也像一个表演,当然不是说它假,虽然它有虚构。它其实有点游戏的感觉,或者说戏剧的成分。它在我看来包含了很多含义。”
8月12日,孙甘露与董强、毛尖、吕嘉在朵云书院·旗舰店畅谈米兰·昆德拉。这是孙甘露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后,第一次在公开活动中露面。
(一)
有关孙甘露,王朔的一句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孙甘露并非中文科班出身。1985年,上海作协举办青年作家讲习班,26岁的邮递员孙甘露与在沪西工人文化宫上班的金宇澄、在商业站搬卸货品的阮海彪、在纺织厂搞机修的程小莹都成为其中一员。讲习班结束,每人要交一篇作品,孙甘露交出了《访问梦境》。
这篇小说于第二年在《上海文学》发表,随即引发热议:这小说特别不像小说。加上后来的《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富有语言实验性的作品,孙甘露和余华、残雪等人一起,作为“1980年代先锋作家”,被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是少年酒坛子》出版那一年,23岁的毕飞宇刚开启写作生涯,那时他以孙甘露为目标:“在先锋文学的层面,余华、苏童和格非在社会层面影响最大,但走得最远的是孙甘露和残雪。孙甘露走到了一种‘荒芜’的地步。”
《我是少年酒坛子》。
然而,先锋小说的“黄金”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用程德培的话说,自1980年代末开始,先锋小说便无人理睬、隐姓埋名。
但先锋小说的退潮似乎并没有影响孙甘露继续走在这条路上。1990年代初,孙甘露依然写出了《音叉、沙漏和节拍器》《忆秦娥》等短篇小说,以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呼吸》。在吴义勤看来,无论读之前的《访问梦境》还是《呼吸》,首先要面对的正是孙甘露那种绝对化的先锋精神方式以及贯穿于这种绝对中的那份令人感动的文学赤诚。
2004年,孙甘露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少女群像》——这是他尚未成形的长篇小说的一个部分。在他自己的讲述里,这篇作品和早期那些通常被描述为实验性的作品不太一样,《少女群像》开始将现实世界呈现到前面。“我想看看现实在我的笔下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我想看看具体的人在这样一个大的动荡的时代背景前面究竟是怎样的,我想处理一下个人命运这种东西。”
然而《少女群像》终究未完。之后近二十年,孙甘露不再发表新的小说。
直到《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二)
昔日的先锋作家要写一部名为《千里江山图》的小说,这个传言在文学圈流传许久。但当它以“谍战”小说的面貌现身,还是狠狠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2020年,一个契机让孙甘露了解到1930年代初非常秘密的一个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如此就是3000里地。
这是历史上非常秘密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
《千里江山图》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2年夏卷。
小说出版后,很多人来问书里的奥秘——最后那封信是谁写给谁的?在小说中至关重要的“浩瀚”有没有原型?那个名叫“穆川”的军官是否另有身份?
作为读者,我自然也有很多猜想。比如,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有何深意?在《呼吸》之后,他为何又一次在长篇小说里引用了《图兰朵》,以及合唱队在序幕中的那句歌词——“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
“写作者在小说中的所有用心,都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去发现。”孙甘露说,关于人物对话的内涵、人物形象的寓意、故事情节的背景、小说细节的设置,很多答案恰恰是在“是”与“不是”之间。
“你不能说‘他就是他’,那这个人物也太无趣了。但你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他’。当然,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有意思,而是‘是’与‘不是’之间,本来就有很多含义。”
“打个比方,生活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爱我吗’,这是很常见的问题。如果另一个人说‘不爱’,未必见得就是不爱,对不对?反过来,如果另一个人说‘爱’,也未必就是爱。问问题的人或许是强迫症,其实并不需要绝对的答案。而回答问题的人,或许自己心里都不清楚到底爱不爱。”
《呼吸》
(三)
我想,这样的回答,本身就很孙甘露。
在近一年多的文学评论和研讨会中,批评家们几乎都会讲到孙甘露的“转型”,讲到他从《访问梦境》到《呼吸》,再从《少女群像》到《千里江山图》的变化。
郜元宝回忆2016年北师大举办的一场关于先锋文学三十年的讨论会,那时文学界对先锋作家转型能否成功的焦虑似乎达到了顶点。“我并不认为孙甘露给先锋文学的转向画了一个句号,但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独特个案。”
孙甘露
孙甘露坦言,《千里江山图》是他接触的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从头至尾,他都视这次写作为全新的学习过程,既是对历史的辨析,也是对历史题材写作的辨析和想象。
在写小说之前,他对当年的社会日常做过大量的资料调研,包括娱乐广告、水文资料、社会新闻、民间八卦等等。它们化为各种背景与伏笔,藏于小说的角角落落,有的如实呈现,有的改头换面,有的被虚构出更多的细节。
这样一次写作,于他也是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
但有些东西依然不变。比如,他依然向往突破概念化的写作,向往对文体的探索。他依然觉得有趣的写法不仅仅是直接交换看法,而有点“顾左右而言他”的意思。他依然对语言的变化和变异感兴趣,依然相信语言的声音、韵律、语调、节奏,都包含了世界的信息。
在今年3月华师大召开的研讨会上,孙甘露说:“我60岁以后,思想上确实发生很大转变。但如果要说什么派,我感觉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我没有变过。”
这句话,连带着小说最后那封没有署名的信,让人们对作为“信使”的孙甘露还有遐想。
(四)
无论阅读旧作还是新作,我都隐隐感觉声音与孙甘露的写作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拿《千里江山图》举例,其中有枪声、爆竹声、脚步声、汽笛声,有各种“大声”和“小声”,还有许多“不作声”。粗略统计一下,全文大约出现了上百种不同的声音。
“在所有感觉里,听觉确实对我影响最大。比如比起文字和画面,音乐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感受。”
《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
孙甘露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爱好就两个,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听广播。而一个男孩对于外部世界最初的想象,恰由广播里那些好听的声音编织而成。
“那时候有个广播节目叫‘长篇连播’,《虹南作战史》《飞雪迎春》《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很多小说,我都是广播里听来的。还有音乐,七十年代我听了很多中国传统音乐,八十年代古典音乐也多了,我最早听到的是贝多芬、舒伯特这些,古典派、浪漫派,都是从广播里听来的。”
说到这里,他有些兴奋地提到自己中学时还做过校园里的广播员。当时的广播站里有唱机,有大盒子一样的录音带,唱片是当时很火的薄膜唱片,他得在老师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放出那些声音。有时他自己也读稿子,现在还能想起一个名叫孔宪凤的“少年楷模”。
当然,少年时代的声音影响不仅于此。后来开始写作,孙甘露发现自己总要读出那些文字。“有时候声音上过不了关,读得不顺,你就觉得写得不对,这成为我的一个习惯。不只是自己的文字,有时候看书也读出来。”
《时间玩偶》书封。
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作家,谈起自己的过往略有卡顿,但一旦聊到那些打动过他的语言,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那时候的处境真是离奇而又悲凉。仿佛置身于高台顶端,飘浮于云雾之中。”(菲利普·索莱尔斯)
“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北纬地区是很常见的。……周围是如此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约瑟夫·布罗茨基)
他坐在那里缓慢地读出这些句子,给我一种无比珍惜的感觉。
(五)
其实,朗读《千里江山图》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我们会发现,在快节奏的“情报博弈”里,那些质朴的、琐碎的、缓慢的日常,也被十分妥帖地安放在文字里。响声不断的爆竹、底楼阵阵的油香、邻居小孩的吵闹,1933年新岁前后的人间烟火,仿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另一重底色。
小说开头,人物依次登场,方位逐个转移,时间紧张推进,一场秘密会议即将展开。在这样连呼吸都紧张的时刻,作家笔锋一转,他写那些秘密工作者们——有人听了一会管弦乐,有人喝了一碗猪杂汤,有人点上了一支烟。
那些拥有秘密职业的人,也是身处生活之中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再成熟的间谍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习惯与偏好,也很可能出错。
之前孙甘露打过一个比方:一个间谍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工作的身份,一个是日常的身份,两者有时重叠,有时分开。“屋子里的一个间谍有一天突然不见了,那么消失的,其实是两个人。”
他希望在这个小说里,人物的个人遭遇、经历成长以及感情,都通过引述,像一个背景一样被带出来。“小说人物,一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之上,不然太抽象;二是被赋予行为动机。小说的难处可能就在于如何揭示动机或者说背后的逻辑,你不能藏得太浅,读者一目了然,就没意思;你也不能藏得太深,读者挖不出来,等于无效。”
自然,读者包含了各种人,如果小说最后归于一个大家无法理解的动机——比如纯粹的人性的恶,那就太乏味了。“它一定要是具体的。而这个很具体的东西又要有一点超乎我们的经验,就是所谓的陌生化。”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无非就是人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但孙甘露相信有的作家有一种命名的能力。
“就像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他不写,很多事情就不存在,就没有被人这样讲过。这个世界像刚刚开端一样,万物都还没有名字,人们看到一个东西指指点点,但叫不出来。但一旦被有的作家写了出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时光硬币的两面》书封。
(六)
不少人也好奇一件事,这么多年没出新作,孙甘露会感到忐忑吗?
“说实在的,忐忑没有,外界什么反应你也没办法。当然你也可以想象,那么多年不写,肯定很多人是蛮好奇的。”他顿了顿说,“但如果我很在意这件事,我就不会那么多年不写,对不对?”
他从不避讳自己是一个写作速度很缓慢的写作者。在散文《自画像》里,他列举过《呼吸》《访问梦境》《信使之函》《请女人猜谜》《仿佛》《忆秦娥》《我是少年酒坛子》《夜晚的语言》《相同的另一把钥匙》……这些作品曾点缀着他的生活,一种松散慵懒的生活,与争分夺秒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
《呼吸》后记中的一句话也仿佛道出了他的秘密:“小说仿佛是一首渐慢曲,它以文本之外的某种速度逐渐沉静下来,融入美和忧伤之中,从而避开所谓需求。”
孙甘露
这一天,孙甘露再一次谈到了自己的“慢”。
“可能也和性格有关,我没觉得自己的写作有多了不起。多写一本,少写一本,在我看来是一样的。换个角度说,我虽然长时间没写,但我一直在读,不单是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我对这个行当是了解的,我对写小说这件事心里也是清楚的。”
当我们从思南走去地铁站,路上说起了漫步。他提到芥川比吕志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无论男女,只要比自己所处的时代稍稍老派一点,都会更有魅力。
说这话的时候,他左手手环的黑色屏幕在阳光下闪了闪光。
那道光仿佛在提醒我,有一种美好在于,无论晴空万里还是刮风下雨,无论周身人群如何飞奔或雀跃,一步一步,一个人总能听见自己内心的时钟,发出的灵魂的声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